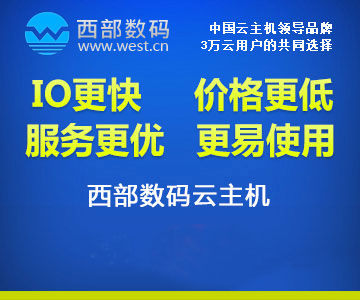《雉舞翚飞歌故乡》 沙占春
时间:2023-02-18 10:33|来源: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编辑:孟凡永|点击:次
天刚放亮,“嘎……嘎……”,颇为清亮的野鸡叫声便或远或近或高或低地不时传来,再加上家养的大公鸡“嗷嗷”地打鸣帮腔,整个村子不多时就聒噪喧闹了起来。
回白城老家闲住,几乎每天都被这大自然的“闹钟”叫醒,尽管很不适应早起,好处却是总能见到初升的太阳,看到成群的牛羊踏着露水赶去很远的草场。
从叫声判断,村子周边至少有十多只公野鸡。只有公鸡才能发出这种极具穿透力的鸣叫,这是它们在各自的地盘上,向母鸡们展示魅力。据此估算,总共要有四、五十只野鸡在村边的树林、草丛、河滩、农田里生活着。
最近的那个家伙应该就在我家大门外。几天下来,我终是忍不住想探个究竟,便顺着院墙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待它的叫声一起,我猛地探出头去——果然,一只色彩艳丽、头高尾长的公野鸡正在沙堆顶上挥洒它的“王者风范”,家养的小鸡则聚拢在它周围刨土啄食。与灰头土脸的家鸡相比,它真有一种鹤立鸡群的高贵优雅。我的突然出现,吓得它乱了阵脚,惊叫一声,猛地扑打翅膀,飞窜到了几十米外的小河套里,留下了一团卷起的尘土和左顾右盼的家鸡。
古书曰翚、学名为雉,环颈雉鸡在老家被叫作“野鸡”,贴切而形象。这只野鸡在这儿呆了三年,已经不怎么怕人,甚至还经常飞到院子里和家鸡抢食吃。和它交过手的大公鸡悉数被它啄得满脸鲜血败下阵来,不敢再与之争锋。它便扬名立万,成了这里的山大王,进而“霸占”了附近几户人家的母鸡,在村里过上了“妻妾成群”的生活。
西院二奎哥告诉我,他家去年孵出了好多只野鸡的后代,虽然花花绿绿的模样很是好看,长大后下蛋却没多大本事,还特别胆小容易受惊,不怎么招人待见。
“估计都是墙外那个家伙的种儿!”二奎说这话时,流露出了顽皮戏谑的神情。
“你小时候不是总打雀吗?这只大野鸡你是不是没打着啊?”我调侃他。
二奎哥的脖子一梗,“你可拉倒吧,以前打雀是为了吃肉,现在肉菜不缺,谁还下得了那狠手。再说,乡里经常到各家各户搞宣传,不准打猎。我都好多年没动那念头了!”
“真的?”
“那还有假,今年春天我家的黄豆苗,全让野鸽子给叨光了,害得我全都补种了一遍。就是这样,我都没出过手。”二奎很是自得,“我闺女不让我伤害野生动物,要保护环境!”
“二奎哥,你这觉悟可真是高啊!”
“不光是我,咱屯子也没人打雀了。这几年你看到咱屯儿的变化没?野鸡兔子到处都是,南边那条细柳河又淌水了,就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大雁、仙鹤都经常能看到了。”
其实,二奎哥说的事我又何尝不知呢。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怎会不感同身受家乡的变化呢?那些发生在父辈和我们身上的故事怎会不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忘呢?
小时候,穷不是我家独有的状况,全村各家各户都不相上下,苞米饼子是主食,土豆白菜是主菜,肉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顿,平时很难闻到肉腥。所以,为吃肉去打鸟便极为平常,甚至理所当然。二奎每次都打得最多也就成了我们淘小子堆里的“英雄”。
野鸡,作为个头最大肉最多的鸟自然成了我们的首选目标。只是这家伙极为聪明机警,似乎能察觉到我们的不轨企图,看到人影便跑得远远的,我们也只能望“鸡”兴叹。于是,我们总会软磨硬泡哀求大人帮忙。虽然生产队里的活计让他们每天都疲惫不堪,但看到我们眼巴巴的样子,有时也会出手相助,所获猎物都成了各家孩子们的“盘中餐”。
老爹是生产队里的放马倌,天一亮就要把牛马群赶到草甸子上吃草,天黑再赶回来饮水进圈。牛马白天吃草时,老爹会有空闲给我们琢磨打雀吃肉。所以,我每天都盼着老爹骑马回来,看马鞍上是不是挂着猎物。不管野鸡或野兔,都是我们兄妹四人的饕餮大餐。尽管这大餐也只能是偶尔为之,但家中老幺的我也吃肉最多的,连二奎哥也没法跟我比。
我就在这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里渐渐长大,村里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也无不面有菜色。而那些野鸡野兔也就在你一只我一只的围追堵截中渐渐消逝了身影。曾几何时,春天里再也听不到公野鸡的高歌,田间林地里也难以见到它们的踪迹。
十八岁那年,我参军离开家乡。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村里实行包产到户,我家分到了一头牛和十六亩地。姐姐写来的家信字里行间都充盈着满足和兴奋。父母和姐姐整天在地里干活,两年下来吃饱穿暖便不成问题,第三年家里养了两头肥猪,卖一头杀一头。姐姐还特意写信告诉我,让我探亲回家吃肉,保准让我吃个够。知道家里的变化,远在边防部队的我也极为高兴,总盼着有休假回家的机会。
提干后的第二年,我坐了三天四宿的绿皮火车终于回家了。那一次,印象最深的便是爹妈和姐姐们脸上的变化――都胖了,都笑了,全然没有了当年的愁苦。即便是后来的三十多年里我经常回来,家里也相继把牛车换成马车,置办了小四轮拖拉机,甚至盖起了四间砖瓦房,但都不及这一次记忆深刻回味绵长,至今还常常在我的梦中重现。
几次春天休假在家,我都有意早起或在地里干活时倾听鸟的叫声,认真判别从头顶飞过的身影是什么品种,但都没能如愿听到野鸡那极具特色的声音,多少有些遗憾。
问过老爹“野鸡咋都没了呢?”老爹叹口气,带着惭愧和伤感,“还不是那些年祸害得太狠了,我们造孽呗!”
“那现在打鸟的人多吗?”
老爹告诉我,现在村里人都忙着种地打工,再加上也不缺吃少穿了,打猎的人自然就少了,“将来野鸡兔子啥的还会回来!”
我试着问:“能吗?”
爹说:“没人再打时保准能再繁殖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从打回家里的电话里,陆续听说村里的猎枪都被收缴了,开始退耕还林还草了,甚至开始夏季禁牧了。一个个无意得到的消息都有一个明晰的指向:村里人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打鸟吃肉已是过去时代的记忆,爱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悄然变成村里人的自动自觉。听说邻县还建立了一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办过一个轰轰烈烈的“白鹤节”。
2009年初春的一天晚上,家里买了电脑,刚刚学会上网的二奎哥在QQ上给我留言:“今天早上我听到村后头有野鸡打鸣了!”
我心头不禁一震——莫不是老爹说的情形真的出现了?马上拨打二奎哥的手机,得到肯定回答后,我竟久久地呆坐在电话机旁。恍惚间,儿时的那些过往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已经辞世安眠在村后林地边上的老爹是不是也听到了?不管他是否地下有知,我一定回家亲口说给他听……
部队命我脱下军装时,我毅然选择回省内工作。自此,回老家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特别是家里有车后,回老家就成了轻松愉快的游玩之旅。一路上树多了草高了,或郁郁葱葱,或硕果累累,或银妆素裹的景象总让我流连忘返,常伫足眺望一番。也会有三五成群的大野鸡或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崽大摇大摆走上公路,再闲庭信步穿行而过,让我又欣喜又紧张,常懊恼自己手慢没能及时取出相机拍下。回老家小住,我喜欢独自到儿时玩过的地方走走看看,模样大多已变了,但那份记忆会更加鲜活。坐在草地上,躺在树荫里,我能听到和从前一样的鸟鸣,我能看到和从前一样的草场,雉舞翚飞,风吹草低。特别是牛群从远处徐徐走近,我仿佛能看到老爹的身影又在挥舞着马鞭,又在吆喝着牲口,只是他的马鞍上不再挂着曾经让我垂涎的“斩获”……
躺在故乡老屋的热炕头上,既温暖舒服又安适恬淡,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想来,我是幸运幸福的,看到了故乡从荒芜破败的落寞闭塞到草长莺飞的欣欣向荣,看到了故乡人从食难裹腹到衣食无忧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这历史变迁的过程虽然漫长,但也正是漫长,才更彰显出这份幸福的可贵。

作者简介:
回白城老家闲住,几乎每天都被这大自然的“闹钟”叫醒,尽管很不适应早起,好处却是总能见到初升的太阳,看到成群的牛羊踏着露水赶去很远的草场。
从叫声判断,村子周边至少有十多只公野鸡。只有公鸡才能发出这种极具穿透力的鸣叫,这是它们在各自的地盘上,向母鸡们展示魅力。据此估算,总共要有四、五十只野鸡在村边的树林、草丛、河滩、农田里生活着。
最近的那个家伙应该就在我家大门外。几天下来,我终是忍不住想探个究竟,便顺着院墙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待它的叫声一起,我猛地探出头去——果然,一只色彩艳丽、头高尾长的公野鸡正在沙堆顶上挥洒它的“王者风范”,家养的小鸡则聚拢在它周围刨土啄食。与灰头土脸的家鸡相比,它真有一种鹤立鸡群的高贵优雅。我的突然出现,吓得它乱了阵脚,惊叫一声,猛地扑打翅膀,飞窜到了几十米外的小河套里,留下了一团卷起的尘土和左顾右盼的家鸡。
古书曰翚、学名为雉,环颈雉鸡在老家被叫作“野鸡”,贴切而形象。这只野鸡在这儿呆了三年,已经不怎么怕人,甚至还经常飞到院子里和家鸡抢食吃。和它交过手的大公鸡悉数被它啄得满脸鲜血败下阵来,不敢再与之争锋。它便扬名立万,成了这里的山大王,进而“霸占”了附近几户人家的母鸡,在村里过上了“妻妾成群”的生活。
西院二奎哥告诉我,他家去年孵出了好多只野鸡的后代,虽然花花绿绿的模样很是好看,长大后下蛋却没多大本事,还特别胆小容易受惊,不怎么招人待见。
“估计都是墙外那个家伙的种儿!”二奎说这话时,流露出了顽皮戏谑的神情。
“你小时候不是总打雀吗?这只大野鸡你是不是没打着啊?”我调侃他。
二奎哥的脖子一梗,“你可拉倒吧,以前打雀是为了吃肉,现在肉菜不缺,谁还下得了那狠手。再说,乡里经常到各家各户搞宣传,不准打猎。我都好多年没动那念头了!”
“真的?”
“那还有假,今年春天我家的黄豆苗,全让野鸽子给叨光了,害得我全都补种了一遍。就是这样,我都没出过手。”二奎很是自得,“我闺女不让我伤害野生动物,要保护环境!”
“二奎哥,你这觉悟可真是高啊!”
“不光是我,咱屯子也没人打雀了。这几年你看到咱屯儿的变化没?野鸡兔子到处都是,南边那条细柳河又淌水了,就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大雁、仙鹤都经常能看到了。”
其实,二奎哥说的事我又何尝不知呢。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怎会不感同身受家乡的变化呢?那些发生在父辈和我们身上的故事怎会不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忘呢?
小时候,穷不是我家独有的状况,全村各家各户都不相上下,苞米饼子是主食,土豆白菜是主菜,肉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顿,平时很难闻到肉腥。所以,为吃肉去打鸟便极为平常,甚至理所当然。二奎每次都打得最多也就成了我们淘小子堆里的“英雄”。
野鸡,作为个头最大肉最多的鸟自然成了我们的首选目标。只是这家伙极为聪明机警,似乎能察觉到我们的不轨企图,看到人影便跑得远远的,我们也只能望“鸡”兴叹。于是,我们总会软磨硬泡哀求大人帮忙。虽然生产队里的活计让他们每天都疲惫不堪,但看到我们眼巴巴的样子,有时也会出手相助,所获猎物都成了各家孩子们的“盘中餐”。
老爹是生产队里的放马倌,天一亮就要把牛马群赶到草甸子上吃草,天黑再赶回来饮水进圈。牛马白天吃草时,老爹会有空闲给我们琢磨打雀吃肉。所以,我每天都盼着老爹骑马回来,看马鞍上是不是挂着猎物。不管野鸡或野兔,都是我们兄妹四人的饕餮大餐。尽管这大餐也只能是偶尔为之,但家中老幺的我也吃肉最多的,连二奎哥也没法跟我比。
我就在这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里渐渐长大,村里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也无不面有菜色。而那些野鸡野兔也就在你一只我一只的围追堵截中渐渐消逝了身影。曾几何时,春天里再也听不到公野鸡的高歌,田间林地里也难以见到它们的踪迹。
十八岁那年,我参军离开家乡。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村里实行包产到户,我家分到了一头牛和十六亩地。姐姐写来的家信字里行间都充盈着满足和兴奋。父母和姐姐整天在地里干活,两年下来吃饱穿暖便不成问题,第三年家里养了两头肥猪,卖一头杀一头。姐姐还特意写信告诉我,让我探亲回家吃肉,保准让我吃个够。知道家里的变化,远在边防部队的我也极为高兴,总盼着有休假回家的机会。
提干后的第二年,我坐了三天四宿的绿皮火车终于回家了。那一次,印象最深的便是爹妈和姐姐们脸上的变化――都胖了,都笑了,全然没有了当年的愁苦。即便是后来的三十多年里我经常回来,家里也相继把牛车换成马车,置办了小四轮拖拉机,甚至盖起了四间砖瓦房,但都不及这一次记忆深刻回味绵长,至今还常常在我的梦中重现。
几次春天休假在家,我都有意早起或在地里干活时倾听鸟的叫声,认真判别从头顶飞过的身影是什么品种,但都没能如愿听到野鸡那极具特色的声音,多少有些遗憾。
问过老爹“野鸡咋都没了呢?”老爹叹口气,带着惭愧和伤感,“还不是那些年祸害得太狠了,我们造孽呗!”
“那现在打鸟的人多吗?”
老爹告诉我,现在村里人都忙着种地打工,再加上也不缺吃少穿了,打猎的人自然就少了,“将来野鸡兔子啥的还会回来!”
我试着问:“能吗?”
爹说:“没人再打时保准能再繁殖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从打回家里的电话里,陆续听说村里的猎枪都被收缴了,开始退耕还林还草了,甚至开始夏季禁牧了。一个个无意得到的消息都有一个明晰的指向:村里人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打鸟吃肉已是过去时代的记忆,爱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悄然变成村里人的自动自觉。听说邻县还建立了一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办过一个轰轰烈烈的“白鹤节”。
2009年初春的一天晚上,家里买了电脑,刚刚学会上网的二奎哥在QQ上给我留言:“今天早上我听到村后头有野鸡打鸣了!”
我心头不禁一震——莫不是老爹说的情形真的出现了?马上拨打二奎哥的手机,得到肯定回答后,我竟久久地呆坐在电话机旁。恍惚间,儿时的那些过往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已经辞世安眠在村后林地边上的老爹是不是也听到了?不管他是否地下有知,我一定回家亲口说给他听……
部队命我脱下军装时,我毅然选择回省内工作。自此,回老家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特别是家里有车后,回老家就成了轻松愉快的游玩之旅。一路上树多了草高了,或郁郁葱葱,或硕果累累,或银妆素裹的景象总让我流连忘返,常伫足眺望一番。也会有三五成群的大野鸡或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崽大摇大摆走上公路,再闲庭信步穿行而过,让我又欣喜又紧张,常懊恼自己手慢没能及时取出相机拍下。回老家小住,我喜欢独自到儿时玩过的地方走走看看,模样大多已变了,但那份记忆会更加鲜活。坐在草地上,躺在树荫里,我能听到和从前一样的鸟鸣,我能看到和从前一样的草场,雉舞翚飞,风吹草低。特别是牛群从远处徐徐走近,我仿佛能看到老爹的身影又在挥舞着马鞭,又在吆喝着牲口,只是他的马鞍上不再挂着曾经让我垂涎的“斩获”……
躺在故乡老屋的热炕头上,既温暖舒服又安适恬淡,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想来,我是幸运幸福的,看到了故乡从荒芜破败的落寞闭塞到草长莺飞的欣欣向荣,看到了故乡人从食难裹腹到衣食无忧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这历史变迁的过程虽然漫长,但也正是漫长,才更彰显出这份幸福的可贵。

作者简介:
沙占春,男,1971年1月生人。吉林镇赉,党员,现任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新闻、散文、诗歌创作近三十年,作品散于国家、省市级报刊杂志。
相关内容
最新资讯
热点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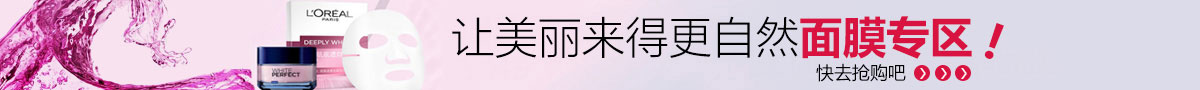




 【会员作品】词二首(词林正韵)
【会员作品】词二首(词林正韵) 【会员作品】我在西北望东北
【会员作品】我在西北望东北 天地春晖近,科普开新元——吉林省科普创作协会元
天地春晖近,科普开新元——吉林省科普创作协会元 【会员作品】松花江
【会员作品】松花江 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1)
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1) 悠悠组诗欣赏
悠悠组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