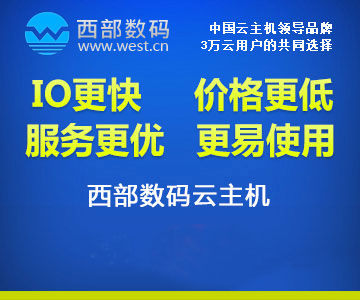蟾 蜍 脸 (小说)
时间:2022-09-24 08:20|来源:《作家》杂志|编辑:网络|点击:次
注:2021年12期《作家》杂志
蟾 蜍 脸
赵 欣
首先必须郑重声明,本故事绝非杜撰。说实话,到今天我仍然感到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任职的那所学校——乌城社会职业大学,时间是2016年9月。
这所学校聘我来教课是因为我是一个势头看好的作家,我以为讲《写作课》非我莫属,但语言文学学院的那个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学究派”的院长交给我的却是一门选修课,叫《民间文学》,名目好听,其实就是讲讲民间流传下来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庞杂得很,里面还有糟粕和不科学的认知,居然在现代社会还保留着顽强的生命力。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教材的导向我是认同的。“老学究派”的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赵老师,试用一学期,好好表现吧!”虽然不尽人意,但对于为生计考虑的我来说,总算有了着落。而且每周一节课,也不累。
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启用了新校址,在距离市区大约七十公里之外的远郊。高校迁移到城市之外,是一个发展态势。市区里剩下的一两所高校,据说也在农村选了新址,正在建设之中。新校建得够规模,够现代化,具备打造一流大学的硬件条件。这在城市里面是受限制的,而乡镇因为发展需要,给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对于民办大学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好事。整个建筑群占地九十多万平方米,可谓“航母”校园。只有一条通向外边的马路,被衬托得格外纤细。若是远远望去,在广袤的农田中间,“航母”校园则是太平洋中的一叶扁舟。
学生宿舍楼那边的围墙外是一大片坟区,石碑、褪色的花圈、冥币焚烧的残迹,住在二楼以上的学生们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情绪,所以住在一楼是幸运的。一楼只给女生住,每当听到男生们煞有其事地描述他们的不适、恐慌或者昨夜的噩梦,她们多少都会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或是侥幸的微笑。
一位男生不甘地站出来,指指地下,又指指远处的坟地,大声宣布说:“别得意,你们知道吗,这里曾经是一整片的坟地!”又指着地下说,“这下面都是坟,只是深埋了而已!”女生们立时就禁了声,脸色泛白,面面相觑。
一位女生甩掉抓住她胳膊的那只手,霍地站起来,质问道:“你是从海南来的,咋知道这么清楚?胡说八道!”
一片哄笑声中,男生涨红了脸,嗫嚅着说:“肯定是这么回事嘛!”
这位男生叫小哲,学委。女生叫小影。抓她手的,叫小琪。
这是一场小集会,自发的。类似的活动相当普遍,特别是周末,整个校园显得人气旺盛。图书馆是最抢手的地方,早就座无虚席了,需要早早去排长长的队伍。被挡在外边的,就在台阶上铺张报纸或是小垫,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还有的在寝室里,或者在班级固定的教室里集合。运动场上人满为患,好像访民在静坐示威,只留狭小的范围是属于运动健儿的。吸烟的挤在臭烘烘的卫生间里,聚餐般兴趣盎然。凡是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了。你以为学生们热爱学习、热衷于学术研讨或是文体活动,那就错了,就是闲聊乱侃,消磨时光。惹得那些清洁工们一边打扫一边抱怨,有的嫌累干脆威胁要辞职,学校只好增加了人手。学校附近的农民纷纷把房子改造成烧烤店、咖啡厅、酒吧、歌厅,生意一片兴隆。

大学生的生活基本是一个模式。周一到周五上课,周六周日放假。大家就像放风的“囚徒”,呼啦一下子都跑到市区里。逛街、游玩、看电影、会朋友,充分享受假日,第二天一早进入新一轮的学习状态,如此往复。这就说到了这所大学学生们的痛处。新址启用半年之后才通了公共汽车,126路,每天两班,到终点站火车站,需耗时一个半小时。再从火车站转往市区,耗时至少一个小时。这样往返总时间约五个小时,一天所剩无几。学生们向往自由的天性被疲劳和焦躁折磨得渐渐失去耐心,出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126路车也只剩下每天一班。我有几次周末加班,见126路车百无聊赖地停在校门外候客,或是迎面开过来,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影。
学校四围的田野里多是玉米,已是深秋,玉米棒子被收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儿兀自立着,像一支支缴械投降等待发落的部队。半夜里,会有一阵阵风刮过整片田地,有时是呜咽,有时是怒吼。有胆大的男生在玉米刚成熟的时候偷了玉米棒子,找个隐蔽的角落支起炉子烤着吃。农民们来讨说法,他们一开始不肯承认,后来就理直气壮了,喝道:“凭什么说是你家的,有记号吗?”还作势要打。农民就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就和学校交涉。关乎邻里关系,所以学校高度重视,开了大会小会,却收效甚微。有农民家丢了鸡鸭鹅狗,也怀疑是学生干的。
所以一说到这所大学,当地人就会气恼而轻蔑地说:“那也叫大学,都什么素质!”有人接话说:“可不是,男生和女生就在玉米地里干坏事,避孕套、卫生纸扔得到处都是!”听者有心,迅速行动,把全家搬到仓房里,把住宅设置了几间客房,果真收益不错。
不知是谁说的,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这话有道理。但小社会一旦处于长期封闭状态,那就会滋生混乱。校园里学生恋爱呈泛滥趋势,多角恋也很常见。殴斗或打群架案件高发,学校的保安力量加强了,也高调处分了几个学生。有人被派出所抓了进去,父母急匆匆从外地赶来摆平。没几天又打坏了人,不过这次他没让父母知道,网贷赔款,没想到到期竟然膨胀了四十倍。贷款公司不找他要,狂轰滥炸他父母的电话,父母报了警,反而激怒了贷款公司,他们又变了招数,不断骚扰辅导员老师和学校领导。这样一来,后果又多了一重,那就是毕业证可能不保,父母只好忍气吞声地拿了冤枉钱。
以上种种,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很重视,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加大引进高校入驻工作的力度,当务之急是对经过谈判、要求过高的那家高校放宽政策。没多久,事情就谈成了。全校师生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大部分村民集体反对,原因就在于我们学校的示范作用。毕竟沾我们光的,只是周边的极少数农民。他们动用农用工具防守,最终连测绘的初期工作都没有完成。短暂的沮丧之后,校园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之后发生了一起学生在课堂上公然抵抗老师的事件,弄得老师狼狈不堪。面对那些戾气十足的学生,我不得不小心翼翼。
言归正传。
我要说的是住在一楼寝室的四个女生,她们的房间号是104,这当然不是我胡编的号码,她们是小影、小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女生,还有小旸、小怡。姓氏隐去。毕竟是女生嘛,惹不出什么大事,更多时间就在寝室里活动,吃零食、喝啤酒、玩游戏、打麻将,或者匆忙抓起一盒安全套赶往某个农家旅店,男友正在那里翘首以待。但这一切,时间一长也就没有意思了,当“囚徒”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学生提出退学,却因为高额学费不予退还而作罢。
这天傍晚,小影和小琪从食堂出来,迎面一对情侣走过来,擦肩而过的时候,小影的目光跟了过去。那对情侣回头,小影对着男生抛了个媚眼,男生愣怔间,女友恼怒地扯了一把,恨恨地看过来。
“瞅啥?下次遇见,帅哥就是我的!”小影用手指推了推眼镜,止步,挑衅地对视。
“快走吧!”小琪用力拉走了她。
回到寝室,其他人还没回来。大家约好了的,要开个故事会,每人讲述自己的情史。这样的故事会开过几次,总觉得不过瘾。上次结束的时候形成一个决议,那就是,谁不把自己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故事说出来,谁就是癞蛤蟆。癞蛤蟆在这里随处可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脚下,稍作停顿就蹦到草丛或是池塘里面去了。
小琪开了门,小影径直走了进去,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你的故事最没劲啦,这次可得来点像样的。”“嗯。”小琪看向小影,“真的要把隐私讲出来么?”
小影拿起手机,眨了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对呀,要不然,有啥意思呢!”见小琪犹豫,又补充说,“感情的事,不就那么一点事儿嘛!有啥稀罕的!我这次给大家来点刺激的!”
“一定还是爱上大叔的故事吧?”小琪笑了,在鼻腔里轻微地哼了一声。
“切!那算什么,这次是基友……哈哈!你又得捂上耳朵听喽!”小影指着小琪大笑。小琪的嘴角动了动,转身去关门。
“妈呀!”小琪突然惊叫了一声,迅速缩到小影的身后,指着门口,颤声说,“小影小影,你看你看!”
小影正在摆弄手机,一边手指麻利地操作着,一边漫不经心地往门口扫了一眼,嘴里嘟囔着:“又咋的啦?一惊一乍的!”话音未落,猛然反应过来,目光再次投射过去,手指离开手机,向上推了推眼镜。
“哎呀妈呀,啥东西呀?癞蛤蟆!”
的确是一只癞蛤蟆,只是这只癞蛤蟆太大了,足有一只脚那么大,它泰然自若地蹲坐在门口,两腮一鼓一鼓的,好奇地看来看去。最奇特的是两只眼睛,就像是两颗深红色的宝石。对面是窗户,因而看起来闪闪亮亮。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从哪里爬过来的呢?
小影的目光兴奋起来,放下手机,慢慢靠近,蹲下去打量着癞蛤蟆。癞蛤蟆毫无怯意,把头昂了昂,大嘴巴微微抿了抿,像是期待着交流。
“赶紧喊人把它弄走吧!”
小琪蹑手蹑脚地靠过来,躲在小影的身后探头探脑地看。
“不,为什么弄走?你觉得碰到这个大家伙容易吗?反正没啥事儿,好好玩玩!”
小影的声音充满恶作剧的狂热,说话间,双脚向前挪了挪,癞蛤蟆没有闪躲,双眼陡然凸出,腹部起伏加剧。小琪的心头蓦然生出一丝恐惧,她忙爬回到自己的床铺上,匆忙间还踩空了一脚。她的床用四根竹竿撑起一顶蚊帐,她拢好蚊帐,脑袋从缝隙中伸出来往下看。
“小琪,给她们两个打电话,买个大垃圾桶回来!”
小影的姿势没动,但声音抛向小琪。
“快点儿!”
她加重了语气,似乎担心癞蛤蟆溜走。小琪探头看了看,癞蛤蟆镇定自若,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影,透出一股说不出的强大气场。
“要垃圾桶干嘛?”
“要大的!别磨叨了,赶紧地!”
小琪打完了电话,很快就听到走廊里啪嗒啪嗒的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小旸、小怡出现在门口。癞蛤蟆对出现在后面的响动并不在意,仅是眨了眨眼睛。
“哎呀妈呀!这么大的癞蛤蟆!”
“哎呀妈呀!成精了是不?它在挑战你吗,小影?”
小旸的手里正捧着一个网状的垃圾桶,小影朝她使了个眼色,她的神经瞬间绷紧,悄悄靠近,弯腰,猛地向癞蛤蟆罩去。小琪听到声音探头看的时候,癞蛤蟆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寝室里爆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笑声里夹杂着顽劣的亢奋。
“我们抓到一只蛤蟆精!”
“一只蛤蟆精!”
“蛤蟆蛤蟆精!”
她们三人围着垃圾桶跳起了舞,跳够了,才注意到小琪,她抖抖索索地缩在纱帘里,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让她们再次爆发出哄笑。
“哈哈哈,胆小鬼!”
“小琪,下来玩儿吧!”
“对呀,小琪,来练练胆儿!”
小琪在她们的招呼声中把蚊帐拉开,在床铺上坐着,看着垃圾桶说:“快放了吧,别玩了,又恶心又可怕!”
小怡说:“恶心啥?不知道癞蛤蟆全身都是宝吗?可以卖钱呢!”
小影说:“你还别说,还没见过这么胆大的家伙,一点儿不怕我们!”
小旸说:“它不怕咱,咱怎么会怕它,就陪它玩玩吧!”
小影向上推了推眼镜框,在寝室里扫视了一周,在小琪的床铺上停住。
“小琪,把你的竹竿给我一根!”
“干什么呀,这是支帐篷的!”
“赶快给我,不然我把癞蛤蟆扔你床上!”
小影狞笑着做出了一个扔的姿势,小琪双手捂住头,求饶说:“别别!”
小影站在梯子上,一把就抽出一根竹竿,帐篷顿时就塌了一角。小琪刚要说什么,小影呲牙咧嘴地对着她的耳朵发出“嘶”的一声,小琪慌忙双手捂住耳朵。
“拍下来,发到网上我们可就成了网红啦!”小怡喊道。
“你负责拍摄!”小影命令小琪说,“要不你就下来参与,否则就把癞蛤蟆扔到你床上!”
“我拍我拍!”小琪的声音带着哭腔,用颤抖的手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
小旸明白了小影的意图,嗖地一下夺过竹竿,蹲下,把头低下,往垃圾桶里瞄去。失去自由,才让癞蛤蟆意识到危险,它不安地蹦来蹦去。
“哈哈,它才知道我们的厉害!”
小影要抢竹竿,小旸商量说:“让我先来嘛!”说话间,已经穿过垃圾桶的网状空隙,把竹竿伸进去,轻轻触了触,癞蛤蟆闪躲着。
“笨呀,我来!”
小影抢过竹竿,用力往里面戳了戳,垃圾桶突然抖动起来。
“快快!别让它跑出来!”小影慌了。
小旸和小怡急忙上前用手死死压住垃圾桶。
“哼,你还敢挣扎?”
小影把眼镜放到床铺上,回来,卯足了劲儿,疯了似的往里面猛戳了一阵,直起腰,大喘着粗气。垃圾桶里面静了下来。鸡血似的阳光照射进来,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图形,像一把沾了血的砍刀。突然,外边起了一股旋风,几片干枯的树叶惊慌地拍打着窗户,似在求救,但很快就被卷走了。
小琪探出半个身子往下看。
“是不是死了?”
三个女生蹲下,歪着头往垃圾桶里看……
突然,垃圾桶向上一拱,小旸和小怡慌忙按住。癞蛤蟆似乎被激怒了,向顶部猛烈冲撞,冲撞了一会儿,发现周边的网状桶壁才是最薄弱的,遂调转方向。它的眼睛更红了,殷红,似乎要渗出血来。眼珠子瞪得大大的,随时要迸射而出的样子。网格出现了破损,裂口变大。三个女生紧张起来,小旸和小怡望着小影,期待她赶紧想出办法来。
小影擦了一把汗,突然想起了什么,跑到自己的床铺,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
“给它喝酒呀?”小旸问,“我们留着喝多好,浪费!”
“玩嘛!这可是高度酒,60度呢!”
“你要烧死它?”小怡的脸上显出残忍的表情。
“不!不!决不可以!”小琪扔掉手机,刚要站起,又意识到会撞到屋顶,就弯了腰,神情严肃、眼神凌厉地看着三个女生,极为坚决地说道:“你们如果那么做,我就告诉老师!”
三个女生吓了一跳,互相对视一眼。
“真他妈的扫兴!”小影嘟囔一句。
小旸说:“还是把它灌醉吧!”
小旸和小怡往小琪的方向看了一眼。
小影不屑地说:“别管她,咱们玩咱们的!”
垃圾桶突然动了起来,癞蛤蟆的嘴钻了出来,小影急忙用竹竿用力戳了戳,癞蛤蟆触电般退了回去,但四肢绷直,腹部膨胀欲爆,蓄势待发。小旸接过小影的酒瓶子,把瓶嘴插进网状空隙,抬高瓶底,一股酒精的味道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
“这样不行!没浇到癞蛤蟆身上!”
小怡说着回到床铺找到一把小刀,在垃圾桶的底部开了个小孔,拿过酒瓶子往口里倾倒。
癞蛤蟆迅速反应,向桶壁再次发起猛攻,小影紧握着竹竿,机警地防守、击退、对峙。也不知过了多久,天黑了,走廊的灯亮了。
小怡伸手按了一下开关,灯亮了,很快又一明一暗地跳闪起来,就在大家以为灯泡要坏掉的时候,亮光稳定下来。
外边的风住了,隐约可以听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过来的喝酒猜拳的声音。窗户黑漆漆一片,映出几个人的影子。垃圾桶再次安静下来。空酒瓶滚到了角落,地面上从垃圾桶那里溢出一滩液体,味道熏人。
“哈哈,癞蛤蟆喝醉了!”
三个女生各伸出一支手,彼此“啪啪”地击掌,又对着小琪的方向做出“耶”的表情。小琪雕塑般僵在那里。
“小琪,你傻了?”小怡问,“你怎么不拍了?”
“赶紧把它弄走吧!”小琪缓过神儿,带着哭腔央求道。
“你怕什么?”小旸说,“不就是一只癞蛤蟆嘛!”
“我们《民间文学》的赵老师不是讲过嘛,在民间,在古时候,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哪!”
小旸笑道:“小琪呀,赵老师也说了,那是当时的民众不懂科学的盲目崇拜嘛!”
“可是,这只癞蛤蟆那么大,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小琪说着把脑袋往后缩了缩,眼神往窗外瞥了一眼,“我们宿舍的墙外就是坟地呀!”
“有关系吗?”三个女生爆发出哄笑。
“你到底是从山沟里来的哈!”小影笑道,“你家那里有狐仙对吧!”
笑过之后,大家的目光回到垃圾桶,它安安静静地倒扣在那里,似乎有什么不正常。三个人蹲下身歪着头,小影的手里紧紧握着竹竿。
“唉呀妈呀!跑啦!”
“真跑啦!”
“啥时跑了?怎么跑的呢?”
小怡把垃圾桶翻过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那只癞蛤蟆出逃的破损处,地面上的液体里面混杂着缕缕鲜红的血迹。
“真是可惜,让它跑了!本来可以卖钱的!”
“是呀,这么大的家伙,本来也可以好好炫耀一下的!”
“就是刚才趁我们不注意时跑的!”
三个女生不约而同地看向小琪,眼神满是责怪。
“怎么能怪我?”小琪低着头嘟囔。
整个过程我当然不在现场。这来自学委小哲绘声绘色的描述,他说是小琪写在QQ日志里的。等我进入小琪的QQ空间里查看的时候,显示已删除。
那天上课,我继续给学生们讲述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有学生举手,我指了一下,她就站了起来。
“老师,这些都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对吗?可是,当今的科学进步越来越有证据挑战那些固有的理论,比如……”
这个学生就是小琪,声音虽小,语气却异常坚定。她停顿了一下,脸上浮出笑意,刻意让问题不那么尖锐。
“老师,历史教科书上说人是猿人在世界各个地方进化而来,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显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母亲,起源于西非,我们该相信哪个?科考人员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发现了诺亚方舟的痕迹,还有人敢说《圣经》是神话吗?有科学家说,大禹治水的故事经过考证确有其事,那么,史书记载黄帝乘龙而去,是不是真的呢?官方认为,龙只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那么1934年辽宁营口坠龙又怎么解释?”
我笑笑说:“你是个好学生,你的超越性思考很好,但是我们得按教材,教材是考试的依据。”
她提问的时候,小影、小旸、小怡就坐在后面一排里面,彼此对视之后同时投过去讥讽的一笑。她们本来都低头玩手机的。这样的课堂现象很常见,不影响我讲课,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次上课的时候,小影、小旸、小怡都请假了,小哲说她们去市里看病去了。什么病我没问,心想无非是感冒之类,或者找个借口游玩去了。之后的课,她们也是旷课,但是有假条。学校明确宣布,私自离开学校后果自负,曾有过女生私自离开学校下落不明的事件。学生的家长来闹事,学校就用这个理由回怼。
她们再次出现在课堂上的时候,都戴着大大的帽子和口罩。这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但供暖很好,并且学校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我感到疑惑。上课的时候,她们三个人不再玩手机,不再交头接耳或者吃东西,而是蔫蔫的、呆呆的。我提问到其中某个人的时候,她先是愣怔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茫然地看着我,歉意地笑着摇摇头。后来小哲告诉我,她们三个都得了一种皮肤病,脸上长满了疙瘩,治疗之后反而严重了。
“废了!”小哲最后总结似地说,“老师,她们彻底废了!男朋友都吓跑了。”
我留了心,几次特意经过她们的座位暗暗观察。她们的口罩很大,几乎遮挡了整个脸部,但是口罩之外的部分仍然可以看出症状。疙瘩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紧密至重叠、凸起,很像癞蛤蟆的背部。小影是最严重的,已经蔓延到脑门和脖子了。脸颊的一侧可以看到块块血痂,里面渗出分泌物来。我判断应该是受不住痒挠坏了。我不敢再看第二眼,心里麻酥酥的。我理解她们的痛苦,作为女孩子,还有比脸面更重要的吗?她们的父母特意赶来,带着她们到北京的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小琪旷课了,小哲说,她退学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我倒是心里轻松了那么一下。这个学生总是发表些莫名其妙的观点,学生们就在下面嗤嗤地笑,对我的课堂秩序有一定影响。
期末考试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罕见的北国风光。已经连续几个冬天很少下雪了,人们似乎已经见惯不怪了。学生们跑到田野里撒欢、打雪仗、堆雪人、拍照片,回到了童年的天真。考场上有三个学生没有参加,正是小影、小旸和小怡。看着贴着名签的空位子,我心里莫名生出无以名状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她们三个原本青春靓丽的形象和后来戴着口罩的样子在我眼前交替浮现。
考试结束,我驾车离开学校,走得很慢,积雪厚得可以没过高腰皮靴,下面是碾压雪地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放眼一望,白茫茫一片,已经分辨不清沟壑了。一阵强风裹挟着雪尘向我的车头袭来,雨刷器自动感应,快速地摆动起来,遮挡了我的视线,车一下子滑到了路边的沟里。任我如何加大油门,车轮只是空转,一股焦糊味道冲击着鼻腔。那些老师们有个大事小情都找学生们去做,而我资历尚浅,担心学生们在事后发帖子揭发,想想还是不惹事为好。四下观望,不远处有一座宅院的残址,是修这条公路时拆迁的房子,还没有彻底拆除清理。
我下了车,走了过去,想找找什么东西可以垫在车轮下面。正好有一堆砖头,我拿到第三块的时候,发现那其实是一个窝,应该是狗窝吧,但现在我看到的是三只青蛙,伏在一个破损的塑料盆里,见到光亮的瞬间,同时张开眼睛定定地看向我。它们的眼睛是红宝石一般的红色,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那三个学生。它们的眼里一下子蓄满了乞求,身体也随着颤抖起来。这样的天气里,估计它们是很难存活的。我思量着应该怎么拯救它们,蹲下身,手伸过去,又烫了似的缩回来——那是三只癞蛤蟆。
我厌恶地站起身,看到身后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看样子也是学校老师,但是我不认识。他们俯着身子,目光还停留在我关注的地方。
“肯定要冻死的。”女的说,她穿着一身毛绒绒的大衣,眼睛很大,有点像关之琳,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女同事,我有点心猿意马。
男的点点头,他也穿着毛绒绒的大衣,矮胖,没有脖子,戴着超大眼镜,嘴巴又宽又厚,绝对像一只蛤蟆。两个人直起身望向我,女的语气很温柔,说:“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冻死的。”余下的话应该是“您赶紧伸出援手吧!”但没说出来。
我往三只癞蛤蟆的身上重重地看了一眼,女的就明白了,她露出微笑,说:“它们其实没那么可怕的。这个状态,怎么可能乱动乱跳呢!”
我暗忖,此时拒绝,从同事的角度来说不大好吧,似乎我没有爱心,以后见了面会尴尬,如果反映到院长那里,那就更糟了。就在我迟疑间,男的弯腰捧起了盆,递给我,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谢谢你呀!”女的声音提高了糖分,满是赞赏和感激。
男的跑在我前面,打开我的车的副驾驶的车门。我说谢谢,就把盆子放在车座上了,其实我本打算放在后备箱里的。我忘了把砖头运过来铺路,上车一启动,车子居然一下子蹿了出来。
停稳车,我打算和那两位同事告别。回头瞅了一眼,却没有看到他们。远望,可见学校影影绰绰的门楼。我突然有种担心,学校会淹没在雪野之中。他们是从学校走过来的吗?又回去了吗?怎么会走得这么快?
一路上我不时观察这三只癞蛤蟆,它们一动不动,正在慢慢复苏吧!那么,把它们安置在哪里呢?也曾闪过把它们扔了的念头,但只是一闪。我是老师,应该是道德的模范。
到了家,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我感受到了暖意。我突然想到,这里不正是它们最好的安置之地吗?我把车在车位里停好,打开侧门,却发现座位上是空的。我忙钻到车里寻找,小心翼翼地,担心触碰到它们那一身可怕的皮肤。但找遍了所有的角落,座椅下面,脚垫下面,后备箱里,也没看到一只癞蛤蟆。我笃定它们就在车里,不可能有机会跑出去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我打开车门的瞬间,整个盆子连同里面的癞蛤蟆掉了出去。我蹲下去,往车和地面之间的空间看去,漆黑之中有两盏绿莹莹的灯照射过来。我吓了一跳,定定心神,两盏灯倏然消失,一团黑影“噌”地蹿出去,很快没了踪影。应该是一只野猫。白天的时候,停车场的光线会好些。但第二天的早上,我只在车体的下面看见一滩机油的痕迹。那个破损的塑料盆呢?扩大范围看了看,也没发现。不远处是个大垃圾桶,里面空空的,应该是刚刚清理过。
那两位同事,特别是那个女的,我再也没有碰见过。会场和食堂这类教师聚集的场合,我改变了不愿意参加的毛病,从未缺过席。甚至还特意查看了各个部门的公示板,那上面有教工的照片,但没有收获。104寝室没有人住,就那么空着。一抬眼就看见坟地的最胆大的男生,也不愿意搬进去住。
我呢,还在这所大学里教《民间文学》。院长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找我谈话,我满心欢喜,以为把《写作课》给我了呢!他探查的目光透过眼镜框盯着我的脸说:“这学期你要承担五门课程。”我暗想,一定是学校认为给我的报酬和工作量不相称。说到底,学校毕竟是个人资本投入,怎会白白便宜我呢?看来以后每天都要上课了,但问题是,路途往返太不方便了。院长笑了一下,收回目光,说:“没有问题,已经给你安排了宿舍,一楼104。”我霍地站起来,话到了嘴边突然失语。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很滑稽吧——遭雷击一般,头发竖立,脸色苍白,嘴唇发颤。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赵老师,好好表现吧!”
2018年4月2日
2018年4月19日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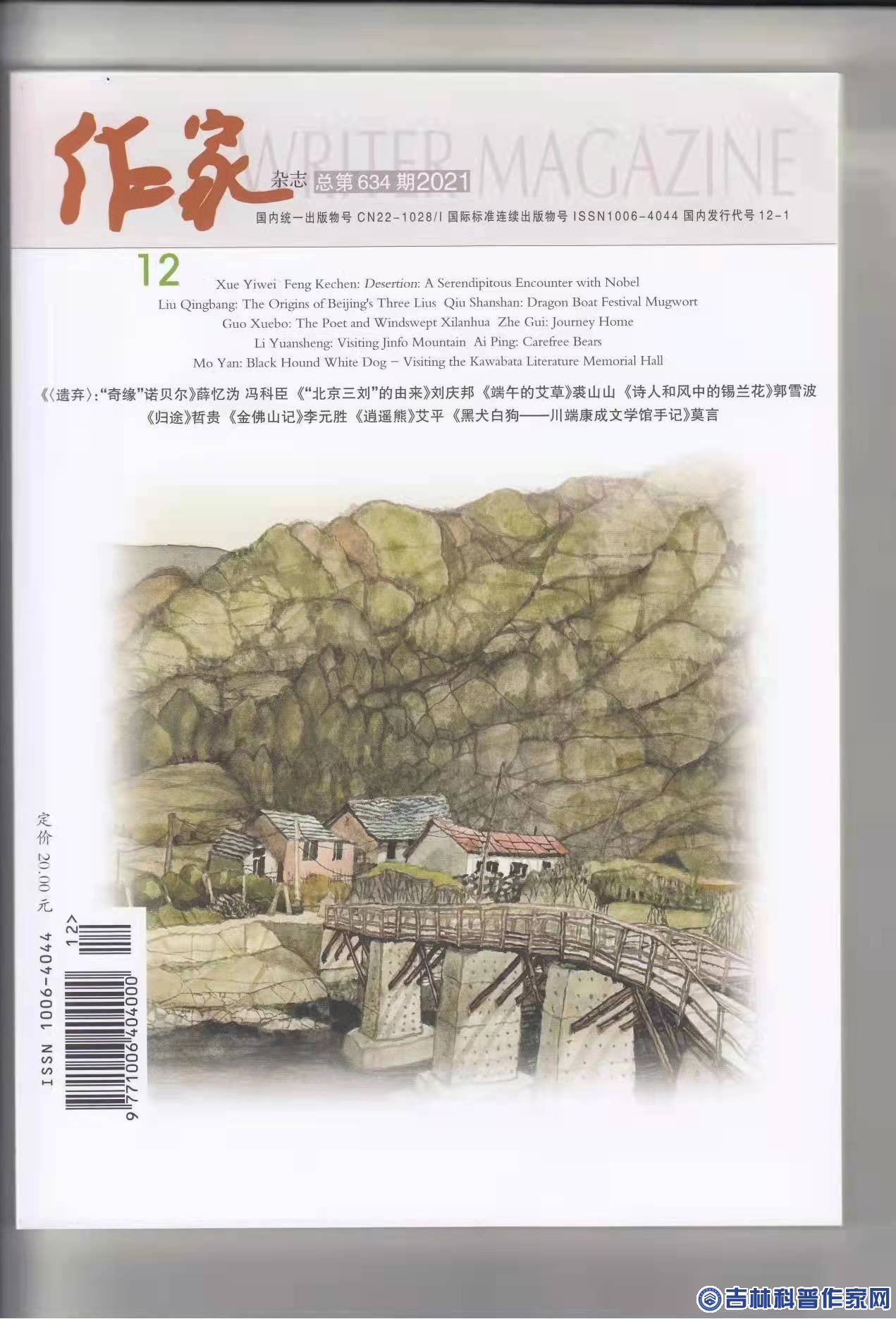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蟾 蜍 脸
赵 欣
首先必须郑重声明,本故事绝非杜撰。说实话,到今天我仍然感到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任职的那所学校——乌城社会职业大学,时间是2016年9月。
这所学校聘我来教课是因为我是一个势头看好的作家,我以为讲《写作课》非我莫属,但语言文学学院的那个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学究派”的院长交给我的却是一门选修课,叫《民间文学》,名目好听,其实就是讲讲民间流传下来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庞杂得很,里面还有糟粕和不科学的认知,居然在现代社会还保留着顽强的生命力。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教材的导向我是认同的。“老学究派”的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赵老师,试用一学期,好好表现吧!”虽然不尽人意,但对于为生计考虑的我来说,总算有了着落。而且每周一节课,也不累。
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启用了新校址,在距离市区大约七十公里之外的远郊。高校迁移到城市之外,是一个发展态势。市区里剩下的一两所高校,据说也在农村选了新址,正在建设之中。新校建得够规模,够现代化,具备打造一流大学的硬件条件。这在城市里面是受限制的,而乡镇因为发展需要,给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对于民办大学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好事。整个建筑群占地九十多万平方米,可谓“航母”校园。只有一条通向外边的马路,被衬托得格外纤细。若是远远望去,在广袤的农田中间,“航母”校园则是太平洋中的一叶扁舟。
学生宿舍楼那边的围墙外是一大片坟区,石碑、褪色的花圈、冥币焚烧的残迹,住在二楼以上的学生们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情绪,所以住在一楼是幸运的。一楼只给女生住,每当听到男生们煞有其事地描述他们的不适、恐慌或者昨夜的噩梦,她们多少都会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或是侥幸的微笑。
一位男生不甘地站出来,指指地下,又指指远处的坟地,大声宣布说:“别得意,你们知道吗,这里曾经是一整片的坟地!”又指着地下说,“这下面都是坟,只是深埋了而已!”女生们立时就禁了声,脸色泛白,面面相觑。
一位女生甩掉抓住她胳膊的那只手,霍地站起来,质问道:“你是从海南来的,咋知道这么清楚?胡说八道!”
一片哄笑声中,男生涨红了脸,嗫嚅着说:“肯定是这么回事嘛!”
这位男生叫小哲,学委。女生叫小影。抓她手的,叫小琪。
这是一场小集会,自发的。类似的活动相当普遍,特别是周末,整个校园显得人气旺盛。图书馆是最抢手的地方,早就座无虚席了,需要早早去排长长的队伍。被挡在外边的,就在台阶上铺张报纸或是小垫,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还有的在寝室里,或者在班级固定的教室里集合。运动场上人满为患,好像访民在静坐示威,只留狭小的范围是属于运动健儿的。吸烟的挤在臭烘烘的卫生间里,聚餐般兴趣盎然。凡是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了。你以为学生们热爱学习、热衷于学术研讨或是文体活动,那就错了,就是闲聊乱侃,消磨时光。惹得那些清洁工们一边打扫一边抱怨,有的嫌累干脆威胁要辞职,学校只好增加了人手。学校附近的农民纷纷把房子改造成烧烤店、咖啡厅、酒吧、歌厅,生意一片兴隆。

大学生的生活基本是一个模式。周一到周五上课,周六周日放假。大家就像放风的“囚徒”,呼啦一下子都跑到市区里。逛街、游玩、看电影、会朋友,充分享受假日,第二天一早进入新一轮的学习状态,如此往复。这就说到了这所大学学生们的痛处。新址启用半年之后才通了公共汽车,126路,每天两班,到终点站火车站,需耗时一个半小时。再从火车站转往市区,耗时至少一个小时。这样往返总时间约五个小时,一天所剩无几。学生们向往自由的天性被疲劳和焦躁折磨得渐渐失去耐心,出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126路车也只剩下每天一班。我有几次周末加班,见126路车百无聊赖地停在校门外候客,或是迎面开过来,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影。
学校四围的田野里多是玉米,已是深秋,玉米棒子被收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儿兀自立着,像一支支缴械投降等待发落的部队。半夜里,会有一阵阵风刮过整片田地,有时是呜咽,有时是怒吼。有胆大的男生在玉米刚成熟的时候偷了玉米棒子,找个隐蔽的角落支起炉子烤着吃。农民们来讨说法,他们一开始不肯承认,后来就理直气壮了,喝道:“凭什么说是你家的,有记号吗?”还作势要打。农民就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就和学校交涉。关乎邻里关系,所以学校高度重视,开了大会小会,却收效甚微。有农民家丢了鸡鸭鹅狗,也怀疑是学生干的。
所以一说到这所大学,当地人就会气恼而轻蔑地说:“那也叫大学,都什么素质!”有人接话说:“可不是,男生和女生就在玉米地里干坏事,避孕套、卫生纸扔得到处都是!”听者有心,迅速行动,把全家搬到仓房里,把住宅设置了几间客房,果真收益不错。
不知是谁说的,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这话有道理。但小社会一旦处于长期封闭状态,那就会滋生混乱。校园里学生恋爱呈泛滥趋势,多角恋也很常见。殴斗或打群架案件高发,学校的保安力量加强了,也高调处分了几个学生。有人被派出所抓了进去,父母急匆匆从外地赶来摆平。没几天又打坏了人,不过这次他没让父母知道,网贷赔款,没想到到期竟然膨胀了四十倍。贷款公司不找他要,狂轰滥炸他父母的电话,父母报了警,反而激怒了贷款公司,他们又变了招数,不断骚扰辅导员老师和学校领导。这样一来,后果又多了一重,那就是毕业证可能不保,父母只好忍气吞声地拿了冤枉钱。
以上种种,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很重视,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加大引进高校入驻工作的力度,当务之急是对经过谈判、要求过高的那家高校放宽政策。没多久,事情就谈成了。全校师生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大部分村民集体反对,原因就在于我们学校的示范作用。毕竟沾我们光的,只是周边的极少数农民。他们动用农用工具防守,最终连测绘的初期工作都没有完成。短暂的沮丧之后,校园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之后发生了一起学生在课堂上公然抵抗老师的事件,弄得老师狼狈不堪。面对那些戾气十足的学生,我不得不小心翼翼。
言归正传。
我要说的是住在一楼寝室的四个女生,她们的房间号是104,这当然不是我胡编的号码,她们是小影、小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女生,还有小旸、小怡。姓氏隐去。毕竟是女生嘛,惹不出什么大事,更多时间就在寝室里活动,吃零食、喝啤酒、玩游戏、打麻将,或者匆忙抓起一盒安全套赶往某个农家旅店,男友正在那里翘首以待。但这一切,时间一长也就没有意思了,当“囚徒”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学生提出退学,却因为高额学费不予退还而作罢。
这天傍晚,小影和小琪从食堂出来,迎面一对情侣走过来,擦肩而过的时候,小影的目光跟了过去。那对情侣回头,小影对着男生抛了个媚眼,男生愣怔间,女友恼怒地扯了一把,恨恨地看过来。
“瞅啥?下次遇见,帅哥就是我的!”小影用手指推了推眼镜,止步,挑衅地对视。
“快走吧!”小琪用力拉走了她。
回到寝室,其他人还没回来。大家约好了的,要开个故事会,每人讲述自己的情史。这样的故事会开过几次,总觉得不过瘾。上次结束的时候形成一个决议,那就是,谁不把自己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故事说出来,谁就是癞蛤蟆。癞蛤蟆在这里随处可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脚下,稍作停顿就蹦到草丛或是池塘里面去了。
小琪开了门,小影径直走了进去,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你的故事最没劲啦,这次可得来点像样的。”“嗯。”小琪看向小影,“真的要把隐私讲出来么?”
小影拿起手机,眨了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对呀,要不然,有啥意思呢!”见小琪犹豫,又补充说,“感情的事,不就那么一点事儿嘛!有啥稀罕的!我这次给大家来点刺激的!”
“一定还是爱上大叔的故事吧?”小琪笑了,在鼻腔里轻微地哼了一声。
“切!那算什么,这次是基友……哈哈!你又得捂上耳朵听喽!”小影指着小琪大笑。小琪的嘴角动了动,转身去关门。
“妈呀!”小琪突然惊叫了一声,迅速缩到小影的身后,指着门口,颤声说,“小影小影,你看你看!”
小影正在摆弄手机,一边手指麻利地操作着,一边漫不经心地往门口扫了一眼,嘴里嘟囔着:“又咋的啦?一惊一乍的!”话音未落,猛然反应过来,目光再次投射过去,手指离开手机,向上推了推眼镜。
“哎呀妈呀,啥东西呀?癞蛤蟆!”
的确是一只癞蛤蟆,只是这只癞蛤蟆太大了,足有一只脚那么大,它泰然自若地蹲坐在门口,两腮一鼓一鼓的,好奇地看来看去。最奇特的是两只眼睛,就像是两颗深红色的宝石。对面是窗户,因而看起来闪闪亮亮。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从哪里爬过来的呢?
小影的目光兴奋起来,放下手机,慢慢靠近,蹲下去打量着癞蛤蟆。癞蛤蟆毫无怯意,把头昂了昂,大嘴巴微微抿了抿,像是期待着交流。
“赶紧喊人把它弄走吧!”
小琪蹑手蹑脚地靠过来,躲在小影的身后探头探脑地看。
“不,为什么弄走?你觉得碰到这个大家伙容易吗?反正没啥事儿,好好玩玩!”
小影的声音充满恶作剧的狂热,说话间,双脚向前挪了挪,癞蛤蟆没有闪躲,双眼陡然凸出,腹部起伏加剧。小琪的心头蓦然生出一丝恐惧,她忙爬回到自己的床铺上,匆忙间还踩空了一脚。她的床用四根竹竿撑起一顶蚊帐,她拢好蚊帐,脑袋从缝隙中伸出来往下看。
“小琪,给她们两个打电话,买个大垃圾桶回来!”
小影的姿势没动,但声音抛向小琪。
“快点儿!”
她加重了语气,似乎担心癞蛤蟆溜走。小琪探头看了看,癞蛤蟆镇定自若,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影,透出一股说不出的强大气场。
“要垃圾桶干嘛?”
“要大的!别磨叨了,赶紧地!”
小琪打完了电话,很快就听到走廊里啪嗒啪嗒的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小旸、小怡出现在门口。癞蛤蟆对出现在后面的响动并不在意,仅是眨了眨眼睛。
“哎呀妈呀!这么大的癞蛤蟆!”
“哎呀妈呀!成精了是不?它在挑战你吗,小影?”
小旸的手里正捧着一个网状的垃圾桶,小影朝她使了个眼色,她的神经瞬间绷紧,悄悄靠近,弯腰,猛地向癞蛤蟆罩去。小琪听到声音探头看的时候,癞蛤蟆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寝室里爆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笑声里夹杂着顽劣的亢奋。
“我们抓到一只蛤蟆精!”
“一只蛤蟆精!”
“蛤蟆蛤蟆精!”
她们三人围着垃圾桶跳起了舞,跳够了,才注意到小琪,她抖抖索索地缩在纱帘里,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让她们再次爆发出哄笑。
“哈哈哈,胆小鬼!”
“小琪,下来玩儿吧!”
“对呀,小琪,来练练胆儿!”
小琪在她们的招呼声中把蚊帐拉开,在床铺上坐着,看着垃圾桶说:“快放了吧,别玩了,又恶心又可怕!”
小怡说:“恶心啥?不知道癞蛤蟆全身都是宝吗?可以卖钱呢!”
小影说:“你还别说,还没见过这么胆大的家伙,一点儿不怕我们!”
小旸说:“它不怕咱,咱怎么会怕它,就陪它玩玩吧!”
小影向上推了推眼镜框,在寝室里扫视了一周,在小琪的床铺上停住。
“小琪,把你的竹竿给我一根!”
“干什么呀,这是支帐篷的!”
“赶快给我,不然我把癞蛤蟆扔你床上!”
小影狞笑着做出了一个扔的姿势,小琪双手捂住头,求饶说:“别别!”
小影站在梯子上,一把就抽出一根竹竿,帐篷顿时就塌了一角。小琪刚要说什么,小影呲牙咧嘴地对着她的耳朵发出“嘶”的一声,小琪慌忙双手捂住耳朵。
“拍下来,发到网上我们可就成了网红啦!”小怡喊道。
“你负责拍摄!”小影命令小琪说,“要不你就下来参与,否则就把癞蛤蟆扔到你床上!”
“我拍我拍!”小琪的声音带着哭腔,用颤抖的手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
小旸明白了小影的意图,嗖地一下夺过竹竿,蹲下,把头低下,往垃圾桶里瞄去。失去自由,才让癞蛤蟆意识到危险,它不安地蹦来蹦去。
“哈哈,它才知道我们的厉害!”
小影要抢竹竿,小旸商量说:“让我先来嘛!”说话间,已经穿过垃圾桶的网状空隙,把竹竿伸进去,轻轻触了触,癞蛤蟆闪躲着。
“笨呀,我来!”
小影抢过竹竿,用力往里面戳了戳,垃圾桶突然抖动起来。
“快快!别让它跑出来!”小影慌了。
小旸和小怡急忙上前用手死死压住垃圾桶。
“哼,你还敢挣扎?”
小影把眼镜放到床铺上,回来,卯足了劲儿,疯了似的往里面猛戳了一阵,直起腰,大喘着粗气。垃圾桶里面静了下来。鸡血似的阳光照射进来,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图形,像一把沾了血的砍刀。突然,外边起了一股旋风,几片干枯的树叶惊慌地拍打着窗户,似在求救,但很快就被卷走了。
小琪探出半个身子往下看。
“是不是死了?”
三个女生蹲下,歪着头往垃圾桶里看……
突然,垃圾桶向上一拱,小旸和小怡慌忙按住。癞蛤蟆似乎被激怒了,向顶部猛烈冲撞,冲撞了一会儿,发现周边的网状桶壁才是最薄弱的,遂调转方向。它的眼睛更红了,殷红,似乎要渗出血来。眼珠子瞪得大大的,随时要迸射而出的样子。网格出现了破损,裂口变大。三个女生紧张起来,小旸和小怡望着小影,期待她赶紧想出办法来。
小影擦了一把汗,突然想起了什么,跑到自己的床铺,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
“给它喝酒呀?”小旸问,“我们留着喝多好,浪费!”
“玩嘛!这可是高度酒,60度呢!”
“你要烧死它?”小怡的脸上显出残忍的表情。
“不!不!决不可以!”小琪扔掉手机,刚要站起,又意识到会撞到屋顶,就弯了腰,神情严肃、眼神凌厉地看着三个女生,极为坚决地说道:“你们如果那么做,我就告诉老师!”
三个女生吓了一跳,互相对视一眼。
“真他妈的扫兴!”小影嘟囔一句。
小旸说:“还是把它灌醉吧!”
小旸和小怡往小琪的方向看了一眼。
小影不屑地说:“别管她,咱们玩咱们的!”
垃圾桶突然动了起来,癞蛤蟆的嘴钻了出来,小影急忙用竹竿用力戳了戳,癞蛤蟆触电般退了回去,但四肢绷直,腹部膨胀欲爆,蓄势待发。小旸接过小影的酒瓶子,把瓶嘴插进网状空隙,抬高瓶底,一股酒精的味道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
“这样不行!没浇到癞蛤蟆身上!”
小怡说着回到床铺找到一把小刀,在垃圾桶的底部开了个小孔,拿过酒瓶子往口里倾倒。
癞蛤蟆迅速反应,向桶壁再次发起猛攻,小影紧握着竹竿,机警地防守、击退、对峙。也不知过了多久,天黑了,走廊的灯亮了。
小怡伸手按了一下开关,灯亮了,很快又一明一暗地跳闪起来,就在大家以为灯泡要坏掉的时候,亮光稳定下来。
外边的风住了,隐约可以听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过来的喝酒猜拳的声音。窗户黑漆漆一片,映出几个人的影子。垃圾桶再次安静下来。空酒瓶滚到了角落,地面上从垃圾桶那里溢出一滩液体,味道熏人。
“哈哈,癞蛤蟆喝醉了!”
三个女生各伸出一支手,彼此“啪啪”地击掌,又对着小琪的方向做出“耶”的表情。小琪雕塑般僵在那里。
“小琪,你傻了?”小怡问,“你怎么不拍了?”
“赶紧把它弄走吧!”小琪缓过神儿,带着哭腔央求道。
“你怕什么?”小旸说,“不就是一只癞蛤蟆嘛!”
“我们《民间文学》的赵老师不是讲过嘛,在民间,在古时候,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哪!”
小旸笑道:“小琪呀,赵老师也说了,那是当时的民众不懂科学的盲目崇拜嘛!”
“可是,这只癞蛤蟆那么大,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小琪说着把脑袋往后缩了缩,眼神往窗外瞥了一眼,“我们宿舍的墙外就是坟地呀!”
“有关系吗?”三个女生爆发出哄笑。
“你到底是从山沟里来的哈!”小影笑道,“你家那里有狐仙对吧!”
笑过之后,大家的目光回到垃圾桶,它安安静静地倒扣在那里,似乎有什么不正常。三个人蹲下身歪着头,小影的手里紧紧握着竹竿。
“唉呀妈呀!跑啦!”
“真跑啦!”
“啥时跑了?怎么跑的呢?”
小怡把垃圾桶翻过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那只癞蛤蟆出逃的破损处,地面上的液体里面混杂着缕缕鲜红的血迹。
“真是可惜,让它跑了!本来可以卖钱的!”
“是呀,这么大的家伙,本来也可以好好炫耀一下的!”
“就是刚才趁我们不注意时跑的!”
三个女生不约而同地看向小琪,眼神满是责怪。
“怎么能怪我?”小琪低着头嘟囔。
整个过程我当然不在现场。这来自学委小哲绘声绘色的描述,他说是小琪写在QQ日志里的。等我进入小琪的QQ空间里查看的时候,显示已删除。
那天上课,我继续给学生们讲述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有学生举手,我指了一下,她就站了起来。
“老师,这些都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对吗?可是,当今的科学进步越来越有证据挑战那些固有的理论,比如……”
这个学生就是小琪,声音虽小,语气却异常坚定。她停顿了一下,脸上浮出笑意,刻意让问题不那么尖锐。
“老师,历史教科书上说人是猿人在世界各个地方进化而来,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显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母亲,起源于西非,我们该相信哪个?科考人员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发现了诺亚方舟的痕迹,还有人敢说《圣经》是神话吗?有科学家说,大禹治水的故事经过考证确有其事,那么,史书记载黄帝乘龙而去,是不是真的呢?官方认为,龙只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那么1934年辽宁营口坠龙又怎么解释?”
我笑笑说:“你是个好学生,你的超越性思考很好,但是我们得按教材,教材是考试的依据。”
她提问的时候,小影、小旸、小怡就坐在后面一排里面,彼此对视之后同时投过去讥讽的一笑。她们本来都低头玩手机的。这样的课堂现象很常见,不影响我讲课,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次上课的时候,小影、小旸、小怡都请假了,小哲说她们去市里看病去了。什么病我没问,心想无非是感冒之类,或者找个借口游玩去了。之后的课,她们也是旷课,但是有假条。学校明确宣布,私自离开学校后果自负,曾有过女生私自离开学校下落不明的事件。学生的家长来闹事,学校就用这个理由回怼。
她们再次出现在课堂上的时候,都戴着大大的帽子和口罩。这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但供暖很好,并且学校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我感到疑惑。上课的时候,她们三个人不再玩手机,不再交头接耳或者吃东西,而是蔫蔫的、呆呆的。我提问到其中某个人的时候,她先是愣怔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茫然地看着我,歉意地笑着摇摇头。后来小哲告诉我,她们三个都得了一种皮肤病,脸上长满了疙瘩,治疗之后反而严重了。
“废了!”小哲最后总结似地说,“老师,她们彻底废了!男朋友都吓跑了。”
我留了心,几次特意经过她们的座位暗暗观察。她们的口罩很大,几乎遮挡了整个脸部,但是口罩之外的部分仍然可以看出症状。疙瘩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紧密至重叠、凸起,很像癞蛤蟆的背部。小影是最严重的,已经蔓延到脑门和脖子了。脸颊的一侧可以看到块块血痂,里面渗出分泌物来。我判断应该是受不住痒挠坏了。我不敢再看第二眼,心里麻酥酥的。我理解她们的痛苦,作为女孩子,还有比脸面更重要的吗?她们的父母特意赶来,带着她们到北京的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小琪旷课了,小哲说,她退学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我倒是心里轻松了那么一下。这个学生总是发表些莫名其妙的观点,学生们就在下面嗤嗤地笑,对我的课堂秩序有一定影响。
期末考试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罕见的北国风光。已经连续几个冬天很少下雪了,人们似乎已经见惯不怪了。学生们跑到田野里撒欢、打雪仗、堆雪人、拍照片,回到了童年的天真。考场上有三个学生没有参加,正是小影、小旸和小怡。看着贴着名签的空位子,我心里莫名生出无以名状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她们三个原本青春靓丽的形象和后来戴着口罩的样子在我眼前交替浮现。
考试结束,我驾车离开学校,走得很慢,积雪厚得可以没过高腰皮靴,下面是碾压雪地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放眼一望,白茫茫一片,已经分辨不清沟壑了。一阵强风裹挟着雪尘向我的车头袭来,雨刷器自动感应,快速地摆动起来,遮挡了我的视线,车一下子滑到了路边的沟里。任我如何加大油门,车轮只是空转,一股焦糊味道冲击着鼻腔。那些老师们有个大事小情都找学生们去做,而我资历尚浅,担心学生们在事后发帖子揭发,想想还是不惹事为好。四下观望,不远处有一座宅院的残址,是修这条公路时拆迁的房子,还没有彻底拆除清理。
我下了车,走了过去,想找找什么东西可以垫在车轮下面。正好有一堆砖头,我拿到第三块的时候,发现那其实是一个窝,应该是狗窝吧,但现在我看到的是三只青蛙,伏在一个破损的塑料盆里,见到光亮的瞬间,同时张开眼睛定定地看向我。它们的眼睛是红宝石一般的红色,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那三个学生。它们的眼里一下子蓄满了乞求,身体也随着颤抖起来。这样的天气里,估计它们是很难存活的。我思量着应该怎么拯救它们,蹲下身,手伸过去,又烫了似的缩回来——那是三只癞蛤蟆。
我厌恶地站起身,看到身后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看样子也是学校老师,但是我不认识。他们俯着身子,目光还停留在我关注的地方。
“肯定要冻死的。”女的说,她穿着一身毛绒绒的大衣,眼睛很大,有点像关之琳,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女同事,我有点心猿意马。
男的点点头,他也穿着毛绒绒的大衣,矮胖,没有脖子,戴着超大眼镜,嘴巴又宽又厚,绝对像一只蛤蟆。两个人直起身望向我,女的语气很温柔,说:“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冻死的。”余下的话应该是“您赶紧伸出援手吧!”但没说出来。
我往三只癞蛤蟆的身上重重地看了一眼,女的就明白了,她露出微笑,说:“它们其实没那么可怕的。这个状态,怎么可能乱动乱跳呢!”
我暗忖,此时拒绝,从同事的角度来说不大好吧,似乎我没有爱心,以后见了面会尴尬,如果反映到院长那里,那就更糟了。就在我迟疑间,男的弯腰捧起了盆,递给我,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谢谢你呀!”女的声音提高了糖分,满是赞赏和感激。
男的跑在我前面,打开我的车的副驾驶的车门。我说谢谢,就把盆子放在车座上了,其实我本打算放在后备箱里的。我忘了把砖头运过来铺路,上车一启动,车子居然一下子蹿了出来。
停稳车,我打算和那两位同事告别。回头瞅了一眼,却没有看到他们。远望,可见学校影影绰绰的门楼。我突然有种担心,学校会淹没在雪野之中。他们是从学校走过来的吗?又回去了吗?怎么会走得这么快?
一路上我不时观察这三只癞蛤蟆,它们一动不动,正在慢慢复苏吧!那么,把它们安置在哪里呢?也曾闪过把它们扔了的念头,但只是一闪。我是老师,应该是道德的模范。
到了家,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我感受到了暖意。我突然想到,这里不正是它们最好的安置之地吗?我把车在车位里停好,打开侧门,却发现座位上是空的。我忙钻到车里寻找,小心翼翼地,担心触碰到它们那一身可怕的皮肤。但找遍了所有的角落,座椅下面,脚垫下面,后备箱里,也没看到一只癞蛤蟆。我笃定它们就在车里,不可能有机会跑出去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我打开车门的瞬间,整个盆子连同里面的癞蛤蟆掉了出去。我蹲下去,往车和地面之间的空间看去,漆黑之中有两盏绿莹莹的灯照射过来。我吓了一跳,定定心神,两盏灯倏然消失,一团黑影“噌”地蹿出去,很快没了踪影。应该是一只野猫。白天的时候,停车场的光线会好些。但第二天的早上,我只在车体的下面看见一滩机油的痕迹。那个破损的塑料盆呢?扩大范围看了看,也没发现。不远处是个大垃圾桶,里面空空的,应该是刚刚清理过。
那两位同事,特别是那个女的,我再也没有碰见过。会场和食堂这类教师聚集的场合,我改变了不愿意参加的毛病,从未缺过席。甚至还特意查看了各个部门的公示板,那上面有教工的照片,但没有收获。104寝室没有人住,就那么空着。一抬眼就看见坟地的最胆大的男生,也不愿意搬进去住。
我呢,还在这所大学里教《民间文学》。院长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找我谈话,我满心欢喜,以为把《写作课》给我了呢!他探查的目光透过眼镜框盯着我的脸说:“这学期你要承担五门课程。”我暗想,一定是学校认为给我的报酬和工作量不相称。说到底,学校毕竟是个人资本投入,怎会白白便宜我呢?看来以后每天都要上课了,但问题是,路途往返太不方便了。院长笑了一下,收回目光,说:“没有问题,已经给你安排了宿舍,一楼104。”我霍地站起来,话到了嘴边突然失语。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很滑稽吧——遭雷击一般,头发竖立,脸色苍白,嘴唇发颤。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赵老师,好好表现吧!”
2018年4月2日
2018年4月19日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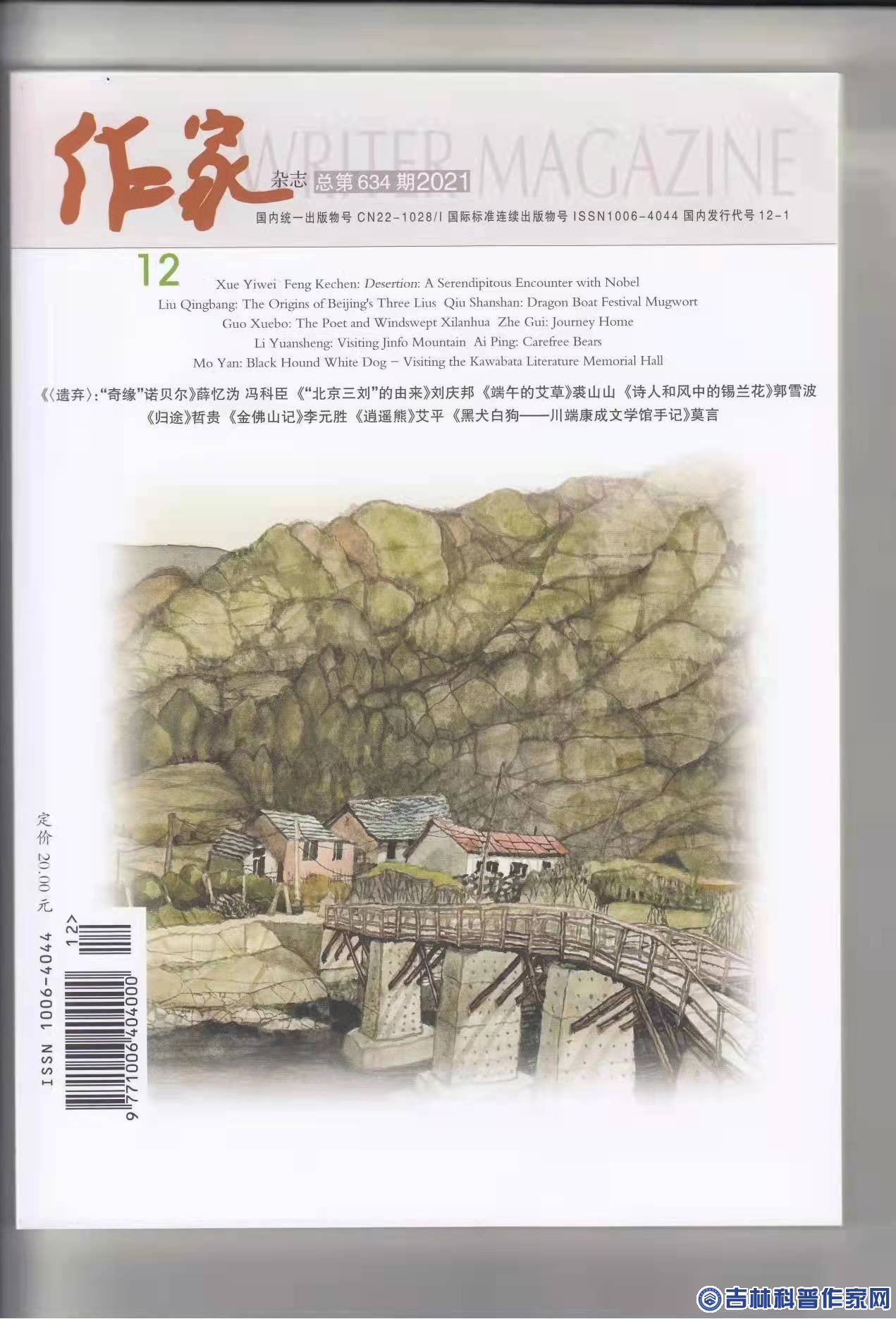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赵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吉林省签约作家,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主席,长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以小说、剧本创作为主,多部作品入选《2016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17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17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等。出版小说集《丈夫的诺言》《回家》《我等着你回来》《空位》4部,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不毕业》。其中《空位》列入长春市委宣传部编撰的新时代长春文学丛书。长篇小说《青春不毕业》,列入吉林省委宣传部编撰的建国70周年献礼(9本)丛书之一。获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五届长春文学奖金奖、吉林文学奖。
2017年跨界影视创作,拍摄微电影、网络大电影20余部,全部获奖。主要影片有《准绳之下》《中秋暖月》《公证于心》《我爸爸是法官》等。奖项有:中央政法委编剧奖、中央政法委最佳影片奖、中宣部优秀微电影奖、亚洲微电影节奖、金风筝国际微电影奖等。
相关内容
最新资讯
热点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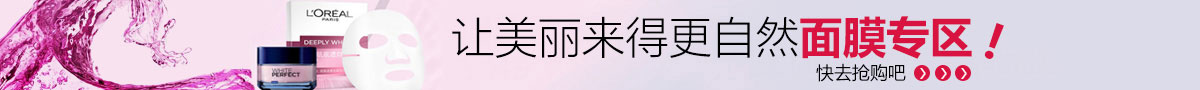











 节气专稿 | 陈耀辉:夏至
节气专稿 | 陈耀辉:夏至 拖鞋(散文)
拖鞋(散文) 葵花籽
葵花籽